蜀地告别蛮夷之风
蜀地告别蛮夷之风

在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四川的学术具有某些地域的特色,而且它与齐鲁之学、关学、洛学、闽学、楚学、徽学等相比较尤有独特的个性而形成了“蜀学”。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蜀学的兴起迄于二十世纪之初,其概念的内涵逐渐丰富和发展,最终成为现代学科之一,此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发端:文翁兴学使蜀地告别“蛮夷之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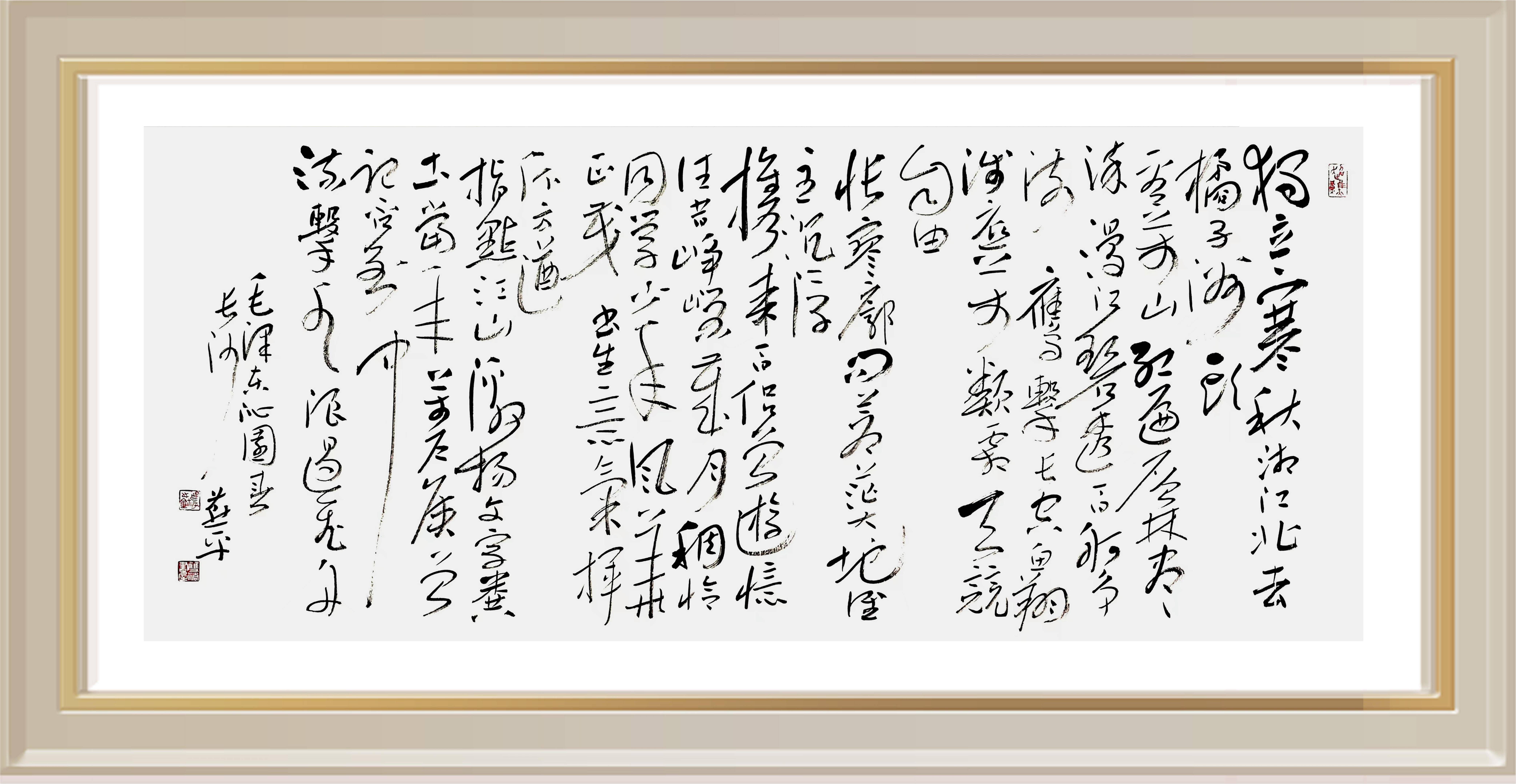
四川在西汉为益州,统辖八郡,其中在川境者计有蜀郡、巴郡、广汉郡、犍为郡、越嶲郡。蜀郡之治所为成都。以上五郡统称蜀地。西汉初年蜀地与中原文化相较是极其落后的蜀地告别蛮夷之风,汉景帝末年(前146—前141)蜀郡郡守文翁治蜀时始采取系列文教措施以改变原有的状况。《汉书·循吏传》记载了文翁在蜀地兴学的事:景帝末,文翁受命任蜀郡守蜀地告别蛮夷之风,文翁以中原文化的眼光见到蜀地仍存“蛮夷之风”,为改革此种情况,特派遣优秀子弟到京都从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学成后回蜀地大力传播儒学。这在中国历史上首创郡国立学官之制,培养地方人才,给文人学士以广阔的政治出路;由此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使蜀地文化在整个汉代文化系统中后来居上,出现了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等文人学者。当时有“蜀文冠天下”之说,《汉书》还记载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晋代蜀中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里也记载了此事。
不过,关于“蜀学比于齐鲁”,据《汉书》所记应理解为蜀地弟子在京师求学者之众,可与齐鲁相比。常璩则表述为张叔等学成后,回蜀中教授子弟,弟子众多,以致蜀中学术之盛可比于齐鲁了,有所不当。常璩的记述虽有失误之处,但西汉时蜀地之文教事业可比齐鲁应是事实,而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蜀学”的概念。这里蜀学是指蜀地文教事业的兴盛和儒学的传播,表明蜀地接受并发展了中原的传统文化。
兴盛:长期的和平环境使蜀学“盛冠天下”
四川学术真正开始呈现地域的特色是在两宋时期。唐末五代时,中原长期战乱,衣冠士族纷纷入蜀避难,前后蜀国获得和平发展的机遇,故至北宋时文教事业极盛。皇佑二年 (1050)田况守蜀时在成都建立经史阁以弘扬学术,吕陶《经史阁记》说:“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吕陶认为西汉成都文翁石室未经兵火战乱的破坏;东汉末高映补修石室作为孔庙,规模宏伟;五代后蜀将《周易》《诗经》《尚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文庙石壁,田况守蜀时又补刻《仪礼》《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这样使儒家经典《九经》完备。因此一千二百余年来,虽然社会历经变革,但蜀中三个神圣遗迹保存完好,它们是蜀学繁盛的标志。吕陶是将蜀学理解为蜀中儒学的。
北宋元佑时期(1086—1093)朝廷中形成三个政治集团,即以苏轼、吕陶、上官均为主的蜀党,以程颐、朱光庭、买易为主的洛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为主的朔党。他们相互进行政治斗争,而蜀党和洛党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史称洛蜀党争。南宋之初统治集团在总结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时清算了王安石变法的政治路线,革除蔡京余党,恢复元佑政治苏轼儒家思想,曾被列入元佑党籍的洛党和蜀党诸公均得以平反昭雪。这时洛党和蜀党已不具政治集团性质,而程颐和苏轼的思想对学术界的影响极大,故“程学”与“苏学”同时盛行。绍兴六年(1136)朝廷开始禁黜程学,被视为“伪学”,而使苏学居于尊崇的地位。南宋中期学术界称“苏学”为“蜀学”。蜀中学者李石《苏文忠集御叙跋》云:“臣窃闻之,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佑学人谓蜀学云。”
苏轼父子治儒家经学,又杂于纵横之学,在北宋古文运动中起到重大作用。他们不同于传统的儒者,既是王安石新学的反对者,又是濂洛理学的否定者,在宋代学术中保持着独立自由的品格与蜀地的学术特色。苏轼、苏辙为领袖,包括黄庭坚、秦观、张耒在内的苏门六君子等人为成员苏轼儒家思想,蜀党的政治活动,贯穿了从仁宗嘉祐到北宋后期,经历了期间大大小小的政治纷争。苏氏蜀学是其思想,苏门则是日后蜀党的主要组成力量。同时,蜀党代表了中后期文坛的最高成就,使这一群体成为文人参政的典型而受到瞩目。因此从南宋以来,蜀学已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思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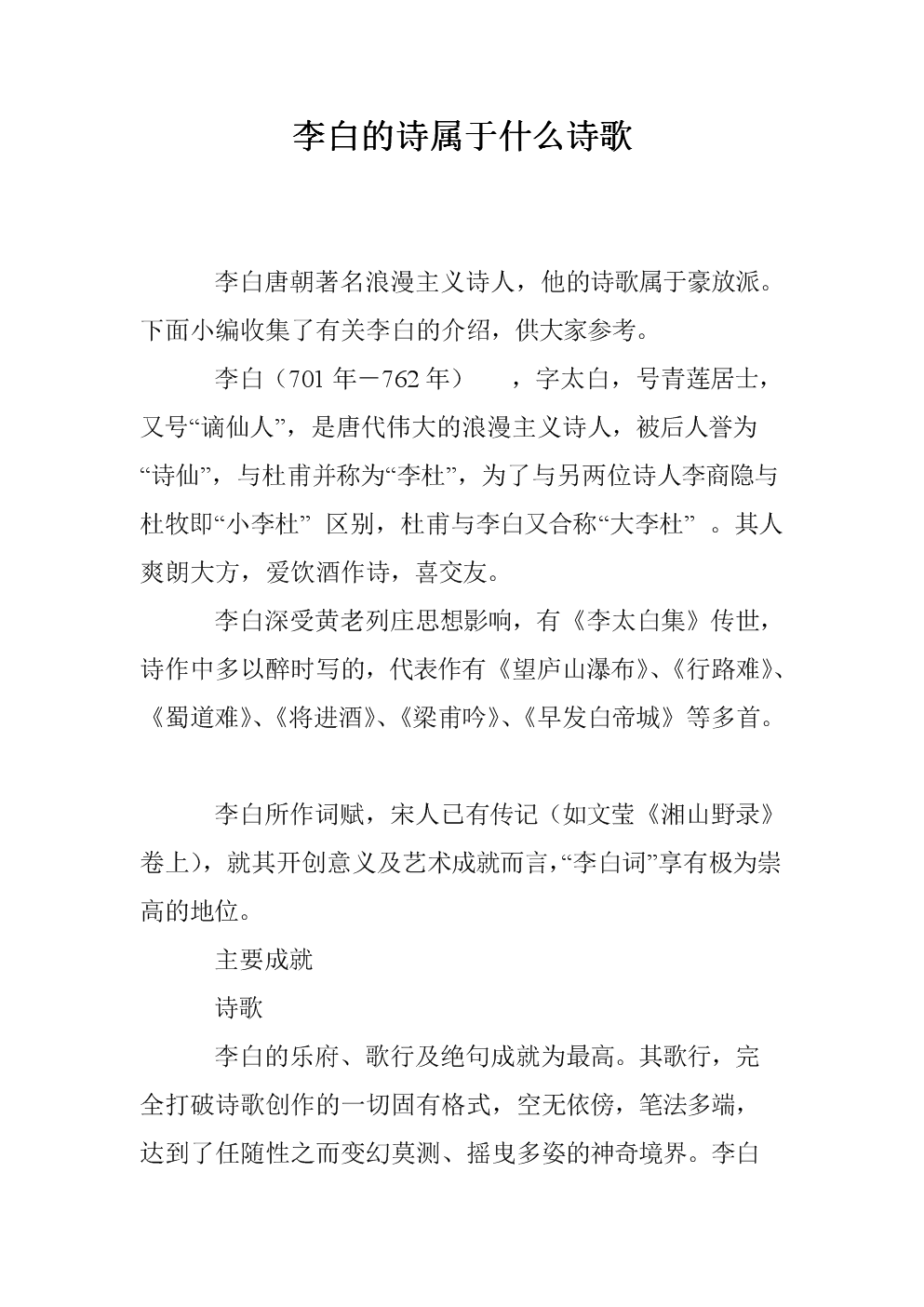
宋以后,蜀学沉寂,直到近代以来,蜀学继宋代之后才又呈后兴之势。这部分内容,我们下期再叙说。
链接
都说李白是诗仙 其实他文章辞赋同样牛
文/清扬
李白是蜀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同时又是我国作家中个性最突出、创作特征最明显、主体意识最鲜明的诗人,他的作品完全打破了传统模式和艺术创作方法。李白作品,自铸伟词,独出新意,而且形式自由不拘,长短随意,气势流走,展示了李白鲜明独到的艺术魅力。后世论者,对李白的作品争论颇多,但对李白特立独行的人格和超然奔放的个性认识,却趋于一致。
李白之所以为读者喜爱,主要是从他的诗歌中获得的感受和认识,李白留下了近千首诗,其实只是“泰山一毫芒”的留存。完整的李白作品,除了诗歌外,尚有文章六十五篇,辞赋八篇。李白的诗很多读者比较熟悉,但对他的的文章辞赋,大众的了解就不多了。
李白的文章反映了极为广阔的现实生活和历史背景,对当时所发生的重大时事均有所触及,而且艺术造诣也很独到,较之于诗篇,更为直观、明晰、具体。《泽畔吟》揭露天宝中晚期的黑暗现实,揭示“惧奸臣之精”“酷吏将至”的惊恐,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将向昏庸的唐朝袭来,那就是“安史之乱”。至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等乱象,在《钱李副使藏用移军广陵序》等文章中,也有所涉及。
李白文章,气势沛然,发端突兀,简练生动,不加雕饰,如《上安州李长史书》开篇即云:“白,嵚崎历落可笑人也。虽然,颇尝览千载、观百家。”开门见山,简扼数语即勾勒出作者身影。余如:“仲尼,大圣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则……”词约义丰,精彩传神。如此落笔,言辞隽洁,出语惊人,如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令人叫绝。
李白文章也秉承了其性格特点,行文自然,纵横奔放,《春夜从弟桃花园序》,堪称千古妙文,令人把玩不已:“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行文流丽,气势沛然,擒纵如意,意到笔随,真可谓抒情文章的逸品。
至于李白的辞赋,虽然只存八篇,却极有气势,如《大鹏赋》《明堂赋》《大猎赋》等,体制宏大,敷衍壮丽,场面恢弘,议论精妙。《大鹏赋》的破题,笔力雄健,气象浑朴,确有“块视三山苏轼儒家思想,杯观五湖”的襟怀。《明堂赋》之巨丽,《大猎赋》之讽谏,都不失为可诵之篇。抒情小赋《拟恨赋》《惜余春赋》《愁阳春赋》《悲清秋赋》以及《剑阁赋》等则呈现出另一风貌,首尾布叙,井然可观。
平心而论,李白的辞赋当然逊色于他的诗歌,但也很可观,只是他文章(包括辞赋)的成就被其诗名所掩盖。读者有兴趣,可看当今较为流行的《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出版,清人王琦注),可有全面了解。
